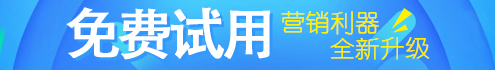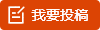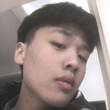這從我的獲獎經歷也可以得到驗證。我一般將自己喜歡的作品和獲獎作品分開看待,這是因為,我個人喜歡的作品,太個性化,多半獲不了獎。這從我二次角逐金像獎的經歷也可以得到驗證,第一次是第六屆金像獎,選送的是二十幅街頭人文攝影作品,寬畫幅的,我準備得極認真,也是自己喜歡的,無論從攝影的新穎性還是社會的深刻性,個人認為都超過我第七屆送評的建筑類作品。但最后是這種沒什么思想內涵的建筑作品獲獎了。后來我給許多評委比較過,他們也認為我的前一組好,但前一組連入選獎都沒評上。你會認為這是個案,其實你只要仔細比較一下歷屆金像獎作品,會發(fā)現(xiàn),這是普遍規(guī)律。就以這屆金像獎評選為例,人民日報的李舸也送了作品,我看過他獲金鏡頭獎的作品,個人認為他的作品比這次獲獎的大多數(shù)作品都要好,無論視覺語言還是社會意義,網(wǎng)上也有不少人為他叫屈就是例證,但他連提名獎都沒評上。這是由于獲獎作品更在乎共同經驗,四平八穩(wěn)的作品更容易被多數(shù)人接受。
然而就是去掉這些因素,這些沙龍獲獎作品,也不是如我們的傳媒,評論家鼓噪的那樣,好得驚世駭俗。比如我在外國的得獎作品,評選應該比較客觀,我們現(xiàn)在還不太有能力把關系搞到國外,別人也未必吃這套。就拿《晨曦》來說,我就認為是個比較僵化的作品,但我按快門的時候我就知道,我拍了一幅獲獎作品,當時我跟同伴說,我拍了一幅金獎作品,他們還以為我在自我鼓勵。后來果然得了金獎,還是在國外得的。并不是我有神機妙算,在這里面混了多年,我太知道它們的游戲規(guī)則了,其實凡這類作品,中外評選標準都差不多。這類影賽,經營多年,已與我們過去科舉的八股文差不多,有一套范式:構圖四平八穩(wěn),最好符合黃金分割法;光影奇妙,越有偶然性越好;畫面略有新意,千萬別太超前,不然有人接受不了,要出奇最好在標題上出奇。
很多人也許會認為,這是評委水評差,看不出好作品,我后來與很多國展、國際展的評委熟了,也想求證這方面的疑惑,私下里和他們聊,發(fā)現(xiàn)他們是很有鑒賞力的,他們的視覺認知,基本是與國際同步的。我有幅作品叫《采石場》,獲的是第十屆中國國際影展評委推薦獎,是當時的評委李前光給的,得獎時我與他不熟,后來一次在一個桌上吃飯,我問他為什么把那寶貴的一票給了我,他說:一二三等獎好不好,不用他一人負責,因為是集體評選的,但評委獎是考驗眼力的,如果不好,別人會笑話的。他還說投了多次,也沒有把這幅作品投入等級獎。連協(xié)會一把手都無法將自己喜歡的作品推入等級獎系列,可見獲獎作品很多時候也并不是由某個人的意志決定得了的。
獲獎作品所以成為今天這種狀況,是由它的體例決定的。這就好比當年的科考文章,評選狀元文章的多半是當朝鴻儒,舉國應試,從唐朝到清朝,竟沒有一篇文章成為文學史的經典。這些評委不是沒有眼光,游戲規(guī)則如此,當文章成了八股,千人一面,就失了它的生命力,誰也不可能玩出奇巧來。就是我們今天的高考“狀元”文章,幾十年了,又有那一篇讓人記住了?從這個角度看,想靠攝影競爭這種方法評出真正有持久感染力的作品,也只能是南轅北轍。
當然,我們應該看到各大沙龍影展對推動攝影的普及是有貢獻的,這幾年,這類展覽也在力圖求新求變,比如國展的紀錄類作品,組照的引入,而金像獎必須是多組作品參評,就是為了使這類評選作品更有社會意義,更能體現(xiàn)攝影人的真實水平。但由于這種綜合展覽出生就帶著胎毒,要想靠這類評獎推出真正的攝影家,流傳青史的攝影作品,也是勉為其難。這類攝影評獎不過是貌視公平的視覺游戲,所以傳媒、評論家要以平常心評介獲獎作品,不要一窩風只叫好,而應該清晰地為這類作品定位。而攝影人要淡化獲獎意識,去浮躁,扎扎實實的拍攝無愧于時代,有思想性的作品。布勒松、弗蘭克、寇德卡等真正世界級的大師,幾乎沒人得過這類世界十杰的獎,但他們的作品就如好酒,越陳越香。偉大的作品由時代說了算,而不會由幾個評委定調調。
當年的科考,一旦金榜提名,其夸耀,比今天的金像獎牛多了,那是真正的上馬金下馬銀,但并不能掩飾其文章的平庸,其實這些人就是做官,政績也是平平,沒見彪柄青史的。同樣,你查一下國展金獎獲得者,又有幾人后來在攝影上做出了成績?我們應理性的對待獲獎作品,真正意識到獲獎作品的局限性。